
易继明
技术理性生长过程中,需要科学伦理的道德约束,否则会成为一种“理性之蚀”,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今年两会期间,新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陈锡文说,“这个问题本身在学界也有非常强的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说它绝对安全或者绝对不安全,所以应当通过实践来证明”。他同时告诉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口一定数量的转基因农产品不可避免,我们自身大豆的产量是1300万吨到1400万吨,但是我们需求的数量超过了7000万吨,仅大豆这一项来说以后还必须进口。”
显然,由陈锡文的讲话而知,转基因食品在中国早已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式的“打嘴仗”,而是已转入了一个“全民试验”的阶段。但问题是,技术发展具有自身的理性,其运用往往具有不可回复的特点;一旦“试验”有误,灾难不可想象。因此,技术理性生长过程中,需要科学伦理的道德约束,否则会成为一种“理性之蚀”,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各种技术帝国主义的论调中,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人们由此产生了技术依赖。我们依存这些专门领域中的专门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而科技本身又欠缺“责任心”;与此同时,社会整合中的宗教、道德的统合能力却在不断地下降,因此人们便希望以对法律关系的信赖为基础,重新复归一种均衡的市民生活状态。这时候的科学技术,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中立性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对自然和对人的统治。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说,“面对这种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那种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维持下去。技术本身不能脱离开技术所赋予的效用。这种工业技术社会是一种已经在各种技术的概念和构成中运转的统治制度”。
马尔库塞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从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显现的(如人的需求的增长、环境破坏、战争残酷等)和隐性的(“虚假的”意识形态、丧失自我、失去自由等)困惑与满足中,发现了技术正在日益增长的巨大作用,特别是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他认为,虽然科技进步的成就避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指控并使合理性的“虚假意识”成为真实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在一定意义上说,发达的工业文化比它的前身是更加意识形态化的”。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这种不合理中存在着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却足以遮蔽人们的视野而使人们忽视其中的不合理性。对此,马尔库塞只得无奈地写道:
我们重新面临发达工业文明中最令人烦恼的一个方面:它的不合理性中的那种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率、它的增加和扩展各种生活舒适品的能力,它的变废物为必需品、变破坏为建设的能力,这种文明把客观世界改造为人的思想和肉体延伸所达到的程度,使得这个异化概念本身成了疑问。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中认识到他们自身;他们在汽车、高保真度的收录机、错层式的住宅和厨房设备中找到了他们的灵魂,把个人栓到社会的这种机制本身已经改变,并且社会控制在它引起的各种新的需要中得到确立。
这些盛行的控制形式,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技术控制。无疑,生产性的和破坏性的设备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功效,一直是使全体居民服从于整个现代确立起来的社会劳动分工的重要手段。更有甚者,这样的一体化,常常伴随着各种更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司法机关、警察、武装力量。现在仍是这样。但是在现时期,各种技术控制手段是为了所有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作为理性的真正体现而出现的。它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技术场景之下,人们成了整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零件,“随大流”地、被迫不停地运转。一个失去了批判精神的社会被精密地组织在一起,人们无法在其中去发现其作为整体或系统的不合理性,也更不可能去对据此构筑的社会进行批判。此时,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现在已不再处于政治系统和社会生活的幕后,而是居于前台,对统治人们发挥着直接的工具性和奴役性的社会功能。并且,科学技术愈发达,人们所受到的奴役和统治程度就愈为深重。于此之际,科学伦理伴随人文主义,必须开启新的社会启蒙运动。
从上述意义上说,技术的解放力量似乎转而成为一种人的解放之桎梏。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将科技作为意识形态还是将科技看成“纯粹性”生产力,都会使我们为了取得另外一种性质的技术而抛弃我们现有的技术。而这种用“二者择一的态度对待自然”的方法,不可能得出一种“新的技术观念”。他说:“我们不把自然当做可以用技术来支配的对象,而是把它作为能够(同我们)相互作用的一方。我们不把自然当作开采对象,而试图把它看做(生存)伙伴。在主体通性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动物、植物,甚至石头具有主观性,并且可以同自然界进行交往,在交往中断的情况下,不能对它进行单纯的改造。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规则是作为一种目的理性的(或工具的和战略的)活动系统。他解释说:“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二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这些预测本身可以被证明是有根据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分析的知识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价值系统)和普遍准则的推论。这些推论或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目的理性的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但是,当工具的活动按照现实的有效控制标准把那些合适和不合适的手段组织起来时,战略活动就只能依赖于正确地评价可能的行为选择了,而正确的评价是借助于价值和准则从演绎中产生的。”
这种分析,改变纯粹的技术分析路径。在克服技术理性、试图保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纯洁性”的倾向中,将以道德为基础的制度框架和以目的理性为基础的科学伦理统一起来。在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中,同时形成了一种富有建构性的理论:科学伦理与技术理性的统合,通过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及其合法性基础,将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以面对科技不断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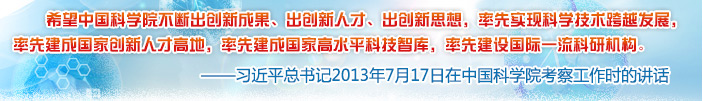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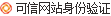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